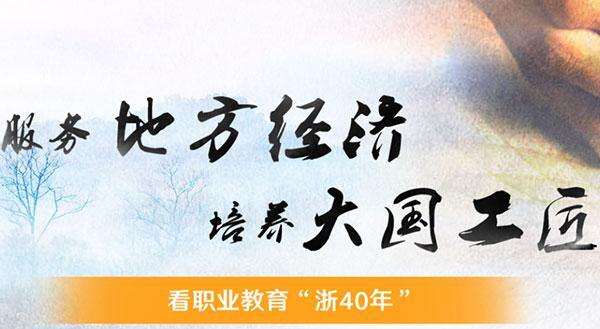被误解的“孤独星球”:融入社会,是他们一生的课题
在浙大儿院康复科的发育评估室里,3岁的苗苗(化名)正拿起一片片不同形状、大小的积木,放进与之适配的孔板中。评估医生一边轻声引导测评流程,一边观察记录着苗苗在各项互动中的行为表现,用以计算最终的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与发育量表的评分。
一旁的妈妈心里五味杂陈。
这不是她第一次带女儿到医院进行孤独症的评估诊断。苗苗一岁多时,同龄的宝宝已经开始牙牙学语,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汇,苗苗却迟迟未开口,也很少跟人有眼神交流互动。
“当时在我们那儿的医院看过,医生说孤独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后来孩子会说话了就停了。现在上了幼儿园,老师反映孩子上课经常乱跑,不听老师的指令,跟别人玩游戏、交朋友也总是出现问题……我家孩子真的是孤独症吗?”这一次,苗苗的妈妈专程带女儿来到浙大儿院康复科主任李海峰的孤独症康复门诊,想要寻得一个确切的答案。
今年的4月2日,是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全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组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为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发病率0.7%,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超过1000万。其中,0至14岁儿童约有300万-500万人,且每年仍在递增。他们也被叫做“星星的孩子”,就像是来自不一样的星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感知着这个世界。

孤独症儿童在接受社交行为干预/图源:浙大儿院
孤独症不等于内向,也并非绝症
早期干预意义重大
近年来,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孤独症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尽管它并不罕见,但人们对它仍存在诸多误解。
李晨曦是浙大儿院康复科的一名主管治疗师。在从事孤独症干预的日子里,她被无数次问道,“我的孩子得孤独症是不是因为我工作忙不陪他?” “是不是我的孩子只是心理问题,性格内向才不说话?”“是不是只要配合治疗,孤独症很快就能治好了……”
面对无所适从的家长,李晨曦不厌其烦地解释着:“孤独症与生俱来且终生存在,既不是心理问题,也不是由带养方式导致的。需要长期干预,现有的科学手段还无法把它完全治愈,只能改善。”
大众眼中的孤独症,往往意味着“自闭”“孤僻”“抗拒社交”,但在孤独症康复门诊中,记者却发现,有些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看起来十分活泼,且个性鲜明。
“临床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孤独症孩子,合并有多动症。”李海峰表示,孤独症涵盖的范围很广,且常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睡眠障碍、癫痫等疾病共患,需进行全面诊断治疗。目前尚缺乏针对孤独症核心症状的特效药,应根据儿童具体情况,采用康复训练、家庭支持和干预及必要的药物对症治疗等综合措施进行干预,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

孤独症儿童在接受社交行为干预/记者 隋雪 摄
而与孤独症干预相关的临床研究与实践也从未停止。“我们目前正在做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的相关研究,通过语言大模型对孤独症儿童进行社交对话干预训练,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将能有效降低康复治疗成本,减轻孤独症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李海峰透露道。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一旦确诊孤独症就没救了,这一辈子都完了,其实一些孤独症孩子得到合适的干预和教育,可以和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融入社会。” 在李晨曦看来,家长应该调整认知,一方面积极寻求专业支持,帮助孩子改善症状,提高能力,另一方面要理解和接纳孤独症孩子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疾病相关的“缺陷”上。“比如很多孤独症孩子的视觉学习能力、对细节的关注能力、遵守规则的能力都比较强,个别能力比较突出的孩子在知识记忆、音乐、绘画等方面还拥有特殊的才华。我们常说的帮孩子融入社会,并不是强行要求孩子一定要变得和普通孩子一模一样,而是包容和尊重孤独症孩子与众不同的特点,帮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

孤独症儿童结构化教学/图源:浙大儿院
“想工作,想找女朋友”
融入社会是他们一生的课题
当“星星的孩子”长大后,又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境遇?
“想找工作,赚钱,想找女朋友,想结婚。”这也许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寻常人生轨迹,但对于23岁的光阳来说,如何才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却是他一生的课题。
光阳3岁开始上幼儿园时,母亲就发现他跟其他孩子似乎不太一样,“喜欢扔东西,塞东西,不是正常孩子玩玩具的样子。”随后,光阳被确诊为孤独症。
孤独症患者并非没有感情,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更加敏感。
随着光阳的长大,母亲逐渐发现,儿子的心理需求几乎与正常孩子无异。“他很善良,很认真。他也渴望与普通人交往,但是其实会碰到很多的挫折。他非常希望表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好的形象,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心理压力就变得巨大。”
今年年初,光阳从大专毕业,但离开了学校,面临的却是不知该何去何从的尴尬与迷茫。“上一次我们去参加残疾人的招聘会,只有一家企业的两个岗位是招收我们这些(孤独症的)孩子的,大部分企业都不接纳。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其实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光阳的母亲说道。
“一直留在家里,有些孩子会退化的。”为了帮助光阳走出焦虑,慢慢融入社会,母亲带他找到了“心星鼓”公益课程。班里有很多和光阳一样“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年龄不同,症状不一,却能以鼓声为媒介建立起心与心之间的交流,结伴成长。在音乐疗愈的过程中,母亲发现光阳也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放松了很多。在一个群体里面,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能被认同,变得更加自信了。”
接受采访时,光阳的母亲曾表示,“希望他能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能够身心放松地生活。当然如果能工作就更好了。”
正值柳枝抽芽的盎然春意里,好消息传来:光阳已经找到了工作,正式踏上人生新篇。
诚然,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但却如同“光阳”的名字一般,始终向着光和太阳的方向,努力生长。
为孤独症人群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支持体系,是一场需要全社会接力的“马拉松”。摘下“异样”的眼镜,愿每个孩子都能如星星般,闪耀在属于自己的广阔夜空。